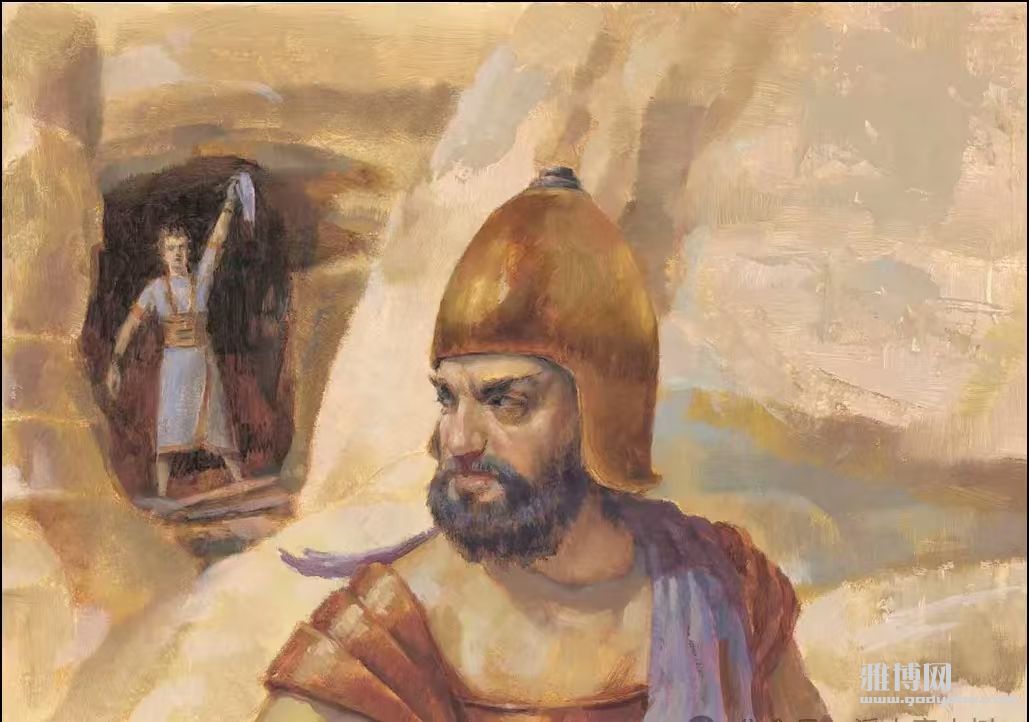中和位育的至善境界——基督的宇宙性救赎及其中国化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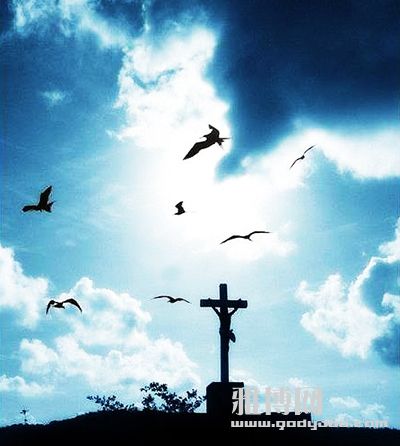
在当代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中,“宇宙的基督”逐渐成为一个跨越宗派、地域与文化的神学主题。该主题不仅回应了现代科学宇宙观的挑战,也拓展了传统基督论的边界。“宇宙的基督”指基督在整个宇宙历史中的救赎性临在,即基督不仅是历史中的拿撒勒人耶稣,还是教会之首,更是全宇宙、全人类、全历史的终极主宰。在基督教中国化的神学探索中,如何推动基督教的救赎论与中华文化的理想境界之间的对话,对基督的宇宙性救赎作中国化的解读,是本文的思考方向。
一、“宇宙的基督”的圣经根据
“宇宙的基督”并非现代神学的新创造,而是深植于新约经文之中。宇宙的基督不仅在起初创造万有,亦在历史中持续维系其秩序与存在,还在末后引导整个宇宙的复和。例如:“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元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里的“万有”具有明显的宇宙性含义,将基督的地位放置在整个宇宙的起源与维系之中。“宇宙的基督”意味着基督不仅是万有的创造者,也是宇宙的救赎者。
二、“宇宙的基督”的神学渊源
基督拯救的不只是人类,还包括整个宇宙,这一教义最初见于早期教父爱任纽“万物同归于一”的救赎论,意思是当基督死而复活升天后,便充满了整个宇宙,不但与宇宙万物同在,更成为其中心,带动整个宇宙向神圣者迈进。奥利金对于《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经文“万物既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上帝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的解释是:“到那时,除了上帝,再也看不到也不保留任何其他东西,上帝必成为一切活动的尺度和标准,所以上帝必成为‘一切’,没有了恶,也不再有任何善恶之别,上帝就是万物,邪恶无一能靠近他。”奥利金的救赎论被称为“万有复归论”。尼撒的格列高利的救赎论深受奥利金影响,认为救赎是“灵魂向上帝的回归”,这种回归永无止境,也永远无法真正达到上帝。不少早期教父相信基督存在于万物之中,因此使万物能联结在一起,这是针对当时异教认为物质世界必会败坏的负面思想而产生的神学回应。当时“宇宙的基督”充满神秘主义色彩,也深化了人、自然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因而发展出丰厚的灵修传统。但是启蒙运动以来,宇宙性基督被批评为迷信及不科学,不少神学家就放弃了宇宙性基督论而转向“历史的基督”。
近代以来,生态危机愈益严重,“宇宙的基督”再一次被提起。法国古生物学家、神学家德日进,在基督教的创造论中吸收了当代进化论思想,并将基督的救赎看作是宇宙进化的动力和终点。他认为,基督作为宇宙的“终极点”,最终引导万事万物结合为一个大的统一体。德日进主张世界还在被造的过程之中,人类与上帝共存于创造的历史中,并且人类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上帝的救赎、教育和圣化。与德日进一样,新教神学家莫尔特曼也吸收了当代进化论的思想,不过他并不完全赞同德日进的过程神学。莫尔特曼批评德日进将“拯救的基督”简单地等同于“进化的基督”,他说,如果简单地以进化的形式来实现拯救,这对于那些进化中的受害者和牺牲者显然是不公的。在莫尔特曼看来,末世论是所有的死者都在末世得救赎中复活和更新,所有的受造物都将获得完满、进入上帝永恒的国,上帝不会遗忘哪怕是最微小的事物。一个只有进化而没有救赎的基督必然是残酷的,基督必须是进化的救赎者,进化过程本身需要基督的救赎。被钉十字架是基督对世界的爱与救赎,基督通过受难让上帝与整个宇宙和好,从而达到宇宙的终极和解和美好和谐的状态,这是无法被进化论吸纳的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三、“宇宙的基督”的中国化解读
中国的先圣先贤们对于宇宙和解与和谐美好状态的理解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不仅描述了天地万物的完美境界,同时也说明了要实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境界,人需要具备的完美的生命状态:“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中庸》认为,人性有其神圣的根源——天命,人的性情生发也应该遵循“天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只有实现了完美的人性,人才能成就其“中和位育”的伟大事工。《大学》对人生使命和方向的论述与《中庸》交相辉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彰显人性的天命明德,不断更新进步,最终使自己和世界均达至完美境界。
《大学》《中庸》关于人性以及其使命的论述与基督教的人论异曲同工。托马斯认为,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可以分享神性存有的最高美善。上帝是宇宙的目的,但宇宙万物通过人趋赴这一目的,因此,人类不但要管理好自己,而且也要与上帝同工,管理引导万物归向上帝。万物归向上帝的美好世界,应该就如同《大学》《中庸》说的“中和位育”的至善境界。
不过,《大学》《中庸》对于宇宙万物和谐至善状态的理解并不是进化论而是救赎论的。《中庸》一方面为我们呈现了宇宙和谐美好的理想境界,另一方面也真诚地感叹:“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道其不行矣夫!”“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说明现实中的人并不具备喜怒哀乐皆中节的“中和”品质,也不可能实现天地位、万物育的理想境界。并且说,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这与基督教的人论不谋而合。在基督教的叙事中,唯有耶稣基督是太初之道、万有真原,唯有他实现了完美人性、达到了喜怒哀乐皆中节的状态,并因其救赎牺牲、死而复活,故能引导一切受造之物复归于上帝,使宇宙万物达至中和位育的至善境界。这与莫尔特曼对于“宇宙的基督”的理解相符,宇宙的基督也是救赎的基督,“中和位育”的实现需要基督的救赎与引导。
总之,“宇宙的基督”这一神学主题,既有坚实的圣经基础与神学传统,又能与中华文化的宇宙观相契合。在中国化神学的语境中,它承载着古老的信仰告白,回应了现代科学的宇宙观,开辟了一条既普世又本土的神学之路。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