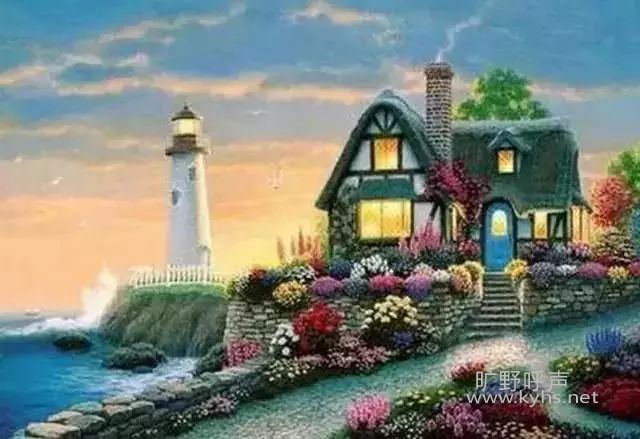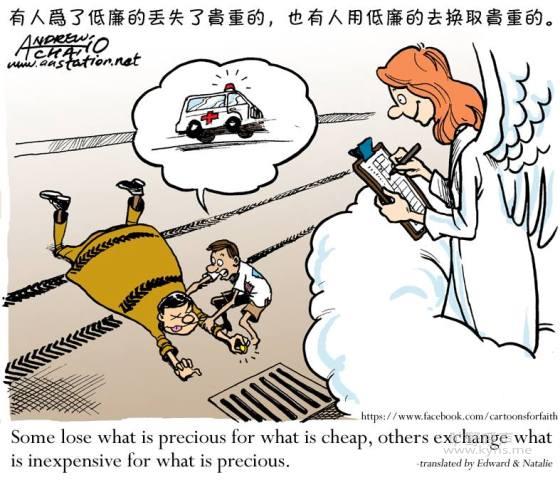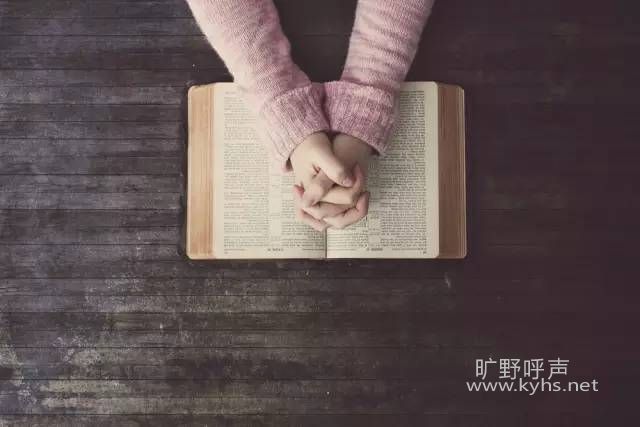感恩节的由来与那些被遗忘的温柔故事
2025-11-25
作者:张远来
来源:雅博网作者我也要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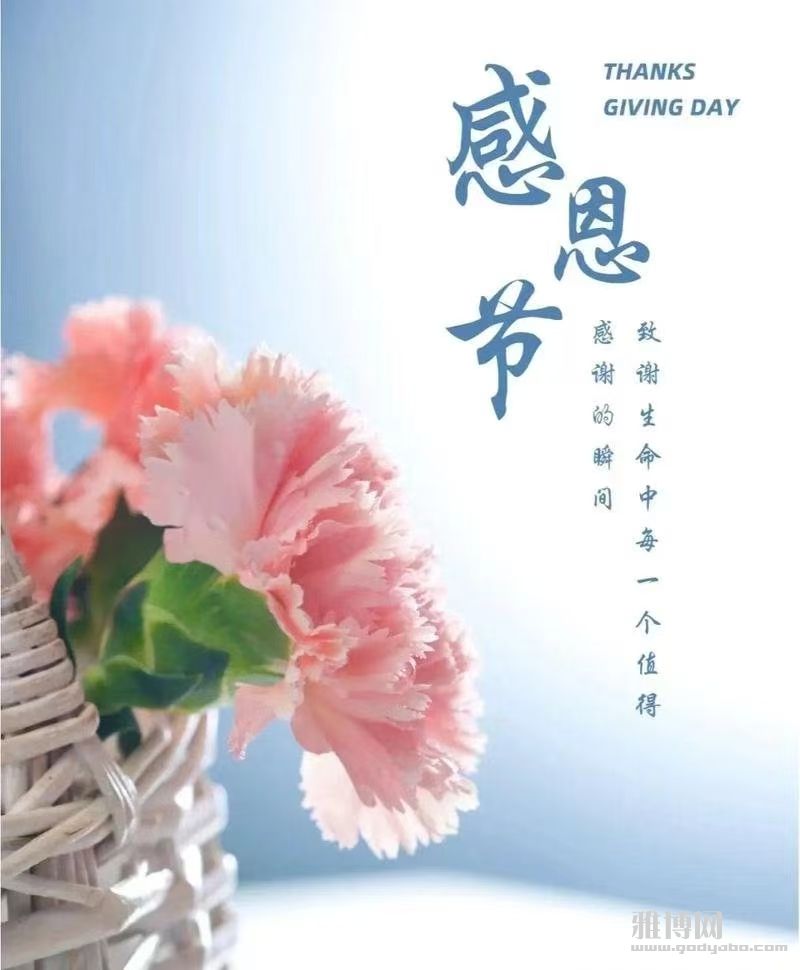
在美国,感恩节是一个会让空气变得温柔的日子。
厨房里烤火鸡的香味从烤箱溢出来,孩子们在电视前为橄榄球比赛吵吵闹闹,老人们围坐在餐桌边,慢慢回忆过去一年的高峰与低谷。
这是今天的感恩节:热闹、丰盛、温馨。
然而,若把这一天的钟表往回拨四百年,穿过城市的灯火、乡村的麦田与州际公路,抵达1621年的普利茅斯海岸,你所看到的将不再是火鸡、南瓜派与家庭团聚,而是一群刚刚经历死亡、风暴与绝望的人,在残破的小木屋旁、在未完全从雪中融化的墓地前,向天举起双手——不是庆祝,而是感恩。
感恩节的开端,不是繁荣,而是破碎。不是胜利,而是劫后余生。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深夜里仍然选择信靠的那份勇气。
愿你准备好,跟我一起走一趟这段早已被浪漫化的旅程。

1621年的普利茅斯海岸
1621年的普利茅斯海岸——感恩节的真实起点
一、从甲板到荒野:一群被连根拔起的人
1620年,102位清教徒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卖掉土地,告别家园,抛下熟悉的城市、教堂与工作,登上一艘破旧的货轮:“五月花号”(Mayflower)。
他们不是移民意义上的“追求更好生活的人”,他们是信仰意义上的旅行者——他们在寻找一个可以自由敬拜、照着良心生活的地方。
横跨大西洋的66天里,他们经历了风暴、疾病、饥饿与晕船:
一名年轻仆人威廉·巴顿(WilliamButten)在抵岸前三天去世;
船上却同时诞生一个婴儿——“奥谢纳斯”(Oceanus)。
生命与死亡在同一个甲板上交织。于是,当五月花号最终靠岸时,船上人数依旧是102人。仿佛上帝在告诉他们:他们的旅程,将总是伴随着失去与新生并存。
二、死亡之冬:感恩节真正的底色不是金黄,而是灰色
很多人以为,感恩节源自“丰收之后的喜乐宴席”。其实,真实的故事更像是一首哀歌。
1620年冬天,被称为“死亡之冬”:
严寒袭来;
饥荒蔓延;
坏血病与FEI炎爆发;
营地每天都有新坟墓;
有时一天要埋两三个人。
最恐怖的时期,全船只有六七人健康,他们要照顾所有生病、虚弱、奄奄一息的人。到了春天,102名清教徒中,只剩下53名幸存者。
他们的第一餐感恩节,并不是“在成功之后感谢”,而是在痛失一半亲人之后仍然选择感谢。他们没有问:“为什么是我们?”他们问的是另一种问题:“在失去一切之后,我们还能抓住什么?”那一年,他们抓住的是——信仰、彼此、契约、与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死亡之冬——感恩节真正的底色
三、被风暴改写的航线:从“原定计划”到“上帝引导”
五月花号的目的地其实不是马萨诸塞州,而是纽约附近的哈德逊河口。那里是英国国王授权的合法殖民地,他们在那里落脚,会有法律保护。但风暴击碎了所有计划。
巨浪把船推离航线,危险的暗礁阻挡他们进入南方水域。在万般无奈中,他们才折返北方,来到普利茅斯海岸。
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全新问题:在没有国王、没有贵族、没有法律的土地上,我们要如何共同生活?
于是,一份改变世界的文件诞生了——《五月花号公约》(MayflowerCompact)——北美第一份民zh u自治契约。
在这份公约中,他们宣告:
我们将彼此立约;
我们按共同制定的法律治理社区;
多数决将成为共同遵守的规范。
这不仅是一个政zh i文件,更是一种神学告白:“在上帝之下,我们彼此负责。”也是一种人生告白:“风暴可以改写航线,但不会取消使命。”很多移民深知这种感觉:原本以为人生会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却被风暴吹向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但经常是:我们以为是失控,上帝却说那是引导。
四、斯匡托:一个被历史忽略,却撑起清教徒希望的孤独灵魂
1621年的春天,清教徒已到了生死边缘。他们不认识这片土地,不会耕种、不懂植物、不熟悉环境,在寒冬之后,连继续活下去的信心也所剩无几。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走进他们的营地,说了一句令所有人惊愕的话:“Welcome,Englishmen.”“欢迎你们,英国人。”他名叫斯匡托(Squanto,本名Tisquantum)。他的存在,像是一场不该出现却出现了的奇迹。
他的故事,比清教徒更悲伤、更震撼:
1614年,他被英国船队诱骗、掳走、卖为奴隶;
在西班牙被修道士救下;
后来辗转到伦敦,与清教徒一起生活,学会英语;
最终回到北美,却发现自己的部落已被疫病灭族。
他是族群唯一幸存者。他站在空荡荡的村落,看着荒草覆盖的土地,意识到自己不再是“离乡的人”,而是一个“已经没有故乡的人”。
他选择帮助,而不是报复。按常理,他完全可以憎恶任何欧洲人。但他没有。他走向这群饥饿、寒冷、绝望的新移民,教他们如何在新英格兰活下去:埋鱼施肥、种玉米;识别危险植物;捕捉鱼类;贮存食物;在荒野中防御危险。更重要的是,他成为清教徒与原住民之间的桥梁。
斯匡托的故事,让感恩节多了一份深邃的忧伤:如果没有他,那一年的清教徒,也许会全部死在普利茅斯。如果感恩节餐桌上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椅子上应该刻着他的名字。

斯匡托——被历史忽略的孤独灵魂
五、一段短暂却珍贵的和平:跨文化的盟约与互助
在斯匡托的斡旋下,清教徒与万帕诺亚格酋长马萨索伊特(Massasoit)签订了互助与和平条约:
不侵略对方;
若谁遭敌攻击,另一方提供援助;
若双方有人犯法或逃跑,愿意按照约定处理;
这段和平持续了五十多年。在北美殖民史极为血腥的背景下,这段关系显得格外珍贵。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在文化冲突不可避免的世界里,选择伸手,会比选择拔剑更难,但也更让人类世界保有人性与尊严。
六、1621年的“三日感恩节”:不是庆典,而是疗伤
到了1621年秋天,清教徒的庄稼获得了第一年的丰收。他们决定举行一个特别的庆典——邀请马萨索伊特和他的90名族人一起参加。
那是一场长达三天的盛宴:
鹿肉(原住民带来五头鹿)
野禽(多半是鹅和鸭)
龙虾、蛤蜊、海鱼
玉米、豆类、蔬菜
游戏、射击比赛、歌唱、祈祷
这不是一顿“成功之后的庆功宴”。这是一群刚刚埋葬一半亲人的人,在幽暗之地中,仍然愿意宣告:“我们活下来了,而活着本身,就是恩典。”

1621年的三日感恩节——不是庆典,而是疗伤
七、感恩节如何成为全国节日?答案隐藏在美国最黑暗的时代
接下来两百多年,感恩节只是地方性的传统。直到1863年的内战时期,美国撕裂成两半,血流成河。在国家痛苦的深处,林肯宣布:每年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为全国感恩日。
不是因为国家顺利,而恰恰是在国家最不顺利的时候,林肯呼吁全国:“让我们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民,好让我们的国家能被医治。”
这就是感恩节的本质:在破碎中寻找恩典,在悲痛中寻找盼望。
八、有温度的“边角故事”:历史的缝隙里,有人性的光
宏大的历史叙事常常让人敬畏,但真正打动人的,是那些藏在历史缝隙中的细节——那些没有写进教科书,却在一个个普通人的生命故事里闪耀的温柔与勇气。感恩节的历史里,也埋着一些容易被忽略,却极其动人的小故事。它们让你知道:感恩节不是“制度塑造的节日”,而是无数普通人用生命写成的节日。
(1)“感恩节之母”莎拉·黑尔:一个女人的17年坚持,改变了一整个国家
莎拉·约瑟法·黑尔(SarahJosephaHale)常常被轻描淡写地提到:“她写过《玛丽有只小羊羔》,也提倡感恩节。”但这句话远不足以描述这位女性的力量。
当她的丈夫因病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时,人们以为她会被困在贫穷与悲痛中。但她选择成为作家、杂志编辑与公共知识分子,在19世纪那个女性声音极不受重视的时代中,她开始提笔,推动一个梦想:让美国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
于是她开始写信——不是写给朋友,而是写给总统:扎卡里·泰勒、米勒德·菲尔莫尔、富兰克林·皮尔斯、詹姆斯·布坎南、最后写给亚伯拉罕·林肯。一写,就是17年。
她在信中说:“战争会让一个国家学会仇恨,但节日可以让一个国家学会感恩。”“一个懂得停下来向上帝感恩的民族,必能在破碎中找到医治。”
当她写这封信给林肯时,美国正撕裂在内战中,北方与南方的母亲,都在哭泣失去儿子的痛苦。林肯在这个时代的最黑暗日子里,收到了这位女性的信,也看到了信后面那个愿景——于是他正式把感恩节设为全国性节日。
一位寡妇、五个孩子、17年的坚持,改变了一整个国家的文化。这节日背后,不只是清教徒的故事,还有一个母亲的眼泪与温柔。
(2)没有南瓜派的第一顿感恩节:缺乏中的分享,是最纯粹的感恩
1621年的第一顿“感恩节大餐”,和我们今天想象的完全不同:没有南瓜派、没有土豆泥、甚至不确定是否有火鸡。
他们有的,是:
鹿肉
野禽——可能是鹅、鸭子、野火鸡
新鲜捕获的海鲜:龙虾、蛤蜊、鳗鱼
玉米饼与蔬菜
野莓、野葡萄、坚果
他们的餐桌可能简陋、破碎、不成体系,他们的食物来自荒野与海岸的恩典,不来自丰裕的供应链。这顿饭的意义不是“吃什么”,而是:在几乎失去一切之后,仍然有“可以共享的人”和“可以共享的食物”。这一餐提醒我们:感恩,不是“够了才感谢”,而是“即使不够,也愿意感谢”。
(3)《铃儿响叮当》的真实故事:两代人之间的幽默与温暖
《铃儿响叮当》(JingleBells)是全世界最广为传唱的圣诞歌曲之一。但它最初根本不是圣诞歌,而是为感恩节主日学写的。
创作者詹姆斯·皮尔庞特(JamesLordPierpont)是一位极具浪漫精神的人。他在马萨诸塞州的雪地里,看着孩子们驾着马拉雪橇奔跑,灵感突然降临。他想写一首:不关于战争、不关于政zh i、不关于痛苦的歌曲。他想写一首——让孩子们想唱,让大人们也能发笑的歌。
于是就有了这一首:“一马敞篷小雪橇呀,叮叮当……”轻快、简单、像童心一般纯净。而后来的故事更温暖:孩子们太喜欢这首歌了,圣诞节时,他们问:“为什么不能圣诞节也唱?”大人们也跟着笑了,于是……圣诞节也唱,新年也唱,甚至年年都唱。最后,这首歌不知不觉变成了圣诞歌。没有人抢,也没有人争,只是因为“爱与欢乐”自然找到最适合它的地方。
在感恩节的众多故事中,这是一份特别的提醒:节日的核心不是历史,而是关系。不是规定,而是共享。
(4)260吨火鸡与电视快餐:一个推销员的灵机一动,改变美国饮食文化
1953年,斯旺森(Swanson)公司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准备了过量的冷冻火鸡,结果感恩节后仓库里堆着260吨卖不出去的火鸡肉。在公司高层即将崩溃时,一位不起眼的推销员格里·托马斯(GerryThomas)提出一个疯狂的点子:他看到一架飞机上的“分格食盒”,突然想到:“如果把火鸡、土豆泥、蔬菜分开装在一个托盘里,让人微波炉加热就能吃,会怎么样?”
公司一听,好像有点道理。于是他们订了5000个铝制托盘,把火鸡和常见的几种配菜分格装好,命名为——“TVDinner”(电视快餐)。意思是:“你可以边看电视边吃。”结果大获成功。美国的家庭饮食文化,从此被改变——微波炉、冷冻食品、快餐式生活方式,由此展开。
所有这一切,都源自:260吨没卖出去的火鸡和一个普通人“我有个点子”。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若你在感恩节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请记得那位推销员。在上帝的手中,小人物也能改写大时代。
(5)富兰克林与火鸡:一封写给女儿的信,藏着父亲的幽默与品格
流传最广的感恩节趣闻之一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想用火鸡当美国国鸟。”事实不是完全这样。他没有提出正式方案,但他确实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吐槽秃鹰:秃鹰偷窃食物、行为懒散、品格不佳(他真的用这个词)。相比之下,他觉得火鸡虽然“有点自负、也有点傻气”,但至少:勤劳、诚实、是真正的美洲原生物种。
富兰克林作为一位政zh i家、科学家、思想家,却在这封信中流露出一种父亲式的幽默与温柔,让人看到历史人物的另一面。这个故事提醒我们:节日不仅属于伟大叙事,也属于日常的家庭对话、父女的笑声、属于那些写在信纸上、不会进历史课本的温暖。
(6)被遗忘的英雄:第一个感恩节上“没有被记录名字的人”
历史书常常把焦点放在领袖或关键人物身上,但在1621年的那张大桌子旁,还有许多名字我们永远不知道、却同样让生命得以延续的人:
在病人身边彻夜照顾的清教徒妇女;
用自己的食物与药草救助陌生人的原住民母亲;
在冬天冒险出海捕鱼的少年;
为陌生文化而担忧、却仍选择伸出援手的族人;
那些在战争与WENYI中保护孩子的父亲;
那些在深夜祷告、没有人听见却改变结果的代祷者。
历史不会为他们立碑,但感恩节本身,就是为他们立的纪念碑。每一个被记住的文明,都是由无数“不被记住的人”撑起来的。感恩节的本质,是为这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献上敬意。
尾声:为什么要讲这些“边角故事”?
因为当大历史让人敬畏,小故事让人柔软。因为当结构让人理解世界,细节让人理解人。因为感恩节从一开始就不是制度,而是关系;不是胜利,而是互助;不是丰盛,而是分享;不是中心,而是边缘;不是英雄,而是所有普通人努力活下来的故事。
愿我们在今年的感恩节里,不仅感恩食物、家庭、健康、成功,也感恩那些无名者、平凡者、小人物——那些历史的边角,却是上帝特别看见的生命。
九、给移民、少数族裔、华人教会的一封信:我们也是“在风暴中寻找归属的人”
这一节,写给所有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因为感恩节的故事,本质就是一个“移民故事”。当我们讲清教徒,我们也在讲自己。当我们讲跨文化和误解,我们也在讲华人群体在美国的处境。当我们讲契约、团契、互助、归属、盼望,我们也在讲我们在异乡如何活出信仰与身份。
1.我们也经历“被风暴迫使改写航线”的人生
很多华人来到北美,不是因为一切计划都顺利:
有人被政zh i与制度逼出来;
有人走在经济压力的缝隙中;
有人为了孩子的未来离乡背井;
有人因为信仰不能在原生土地自由敬拜;
有人是逃离内心深处的不安全。
我们都以为是来“哈德逊河”的,却被风暴推到了“普利茅斯”。感恩节提醒我们:偏航也可能是呼召。
2.我们也常常在“文化边缘”挣扎
语言、习俗、价值观、育儿方式、教育系统、社会结构——这一切都让移民在“熟悉与陌生之间”的灰色地带生活。清教徒第一年在北美的无助,何尝不像无数华人刚抵美国时的经历?我们也经历孤独、文化挫败、身份焦虑。但那不是失败,而是一种深刻的成长。
3.在跨文化关系里,我们既是“清教徒”,也是“原住民”
我们需要别人帮助我们融入土地;但我们也有机会向新移民伸手,成为他们的“斯匡托”;我们需要别人接纳我们的差异;但我们也可以成为社区中的祝福。华人对新移民、对下一代、对少数族裔、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决定了我们将成为一个怎样的群体。一座堡垒?还是一座灯塔?
4.对教会:感恩节提醒我们“教会不是文化俱乐部,而是立约共同体”
北美华人教会常常面临三道裂缝:代际裂缝(父母与孩子)、语言裂缝(中文/英文)、文化裂缝(亚洲文化/美国文化)。很多教会试图用“统一文化”解决这些问题,却常常忽略了:教会的根本不是同文化,而是同福音。
感恩节的故事提醒我们:清教徒与原住民起初不是因为文化一致,而是因为“共同立约”。教会也是如此:靠的是恩典,不是出身。靠的是十字架,不是族群。当华人教会愿意多留一把椅子,北美的属灵图景就会改变。
5.对移民个人:感恩节告诉你,你不是没有家的人
在移民的世界里,“家”常常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在原生文化里,我们不再是完全的“本地人”;在美国文化里,我们永远不完全“属于”;在下一代的眼里,我们像停留在过去;在上一代的眼里,我们又像走得太远。
但感恩节说:“你不是无根的人,你是被上帝带着走的人。”清教徒的家不在英国,也不在普利茅斯,而是在上帝的同在里。因此,移民的归宿不是某块土地,而是一位带领我们走过海洋与风暴的主。
6.感恩节呼唤华人群体:在异乡做“避难所”,不做“隔离墙”
在多族裔的环境中,我们会倾向于留在自己的文化安全区。但清教徒与原住民的那张大桌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安全,是愿意给别人留位置。
愿华人教会在北美成为:新移民可以倾诉的地方;弱势群体可以找到希望的地方;青少年可以找到身份的地方;文化差异可以被理解的地方;属灵生命可以被滋养的地方。
愿我们在这片土地上不是“漂泊者”,而是“祝福者”。
十、尾声:感恩节不是成功者的庆功宴,而是风暴幸存者的敬拜
走到文章的尽头,我们重新看到了感恩节的本质:感恩节的开端不是丰盛,而是缺乏;不是顺利,而是偏航;不是胜利,而是哭泣;不是完成,而是未完成。
因此,感恩节也是为你预备的,无论你今天身处顺境,或正走在生命的“死亡之冬”。
感恩不是在完美中学会的,而是在破碎中选择的。
愿这个感恩节,我们都能:
在忙碌中停下来,看见恩典;
在疲惫中承认,我们仍然被托住;
在移民的漂泊中看见归属;
在文化差异中选择爱;
在异乡的道路上活出使命;
在风暴之中仍然数算恩典。
愿我们在自己的餐桌旁,也多留一把椅子——为新移民、为下一代、为弱势者、为需要的人……也为那位曾经在荒野中与清教徒同行、如今仍与我们同行的主。
愿您在感恩节重温历史与恩典
愿我们记得那些被遗忘的温柔
愿我们成为彼此的斯匡托
在异乡,也在归途
愿恩典常伴
【作者简介】
 张远来:雅博网作者,现居广州。本人为专职牧师,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借古鉴今》、《危机与契机》、《中国教会体制的反思》、《灵恩运动反思》、《我信故我思》、《广州教会发展现状》等。
张远来:雅博网作者,现居广州。本人为专职牧师,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借古鉴今》、《危机与契机》、《中国教会体制的反思》、《灵恩运动反思》、《我信故我思》、《广州教会发展现状》等。
[ 赞一下: ]